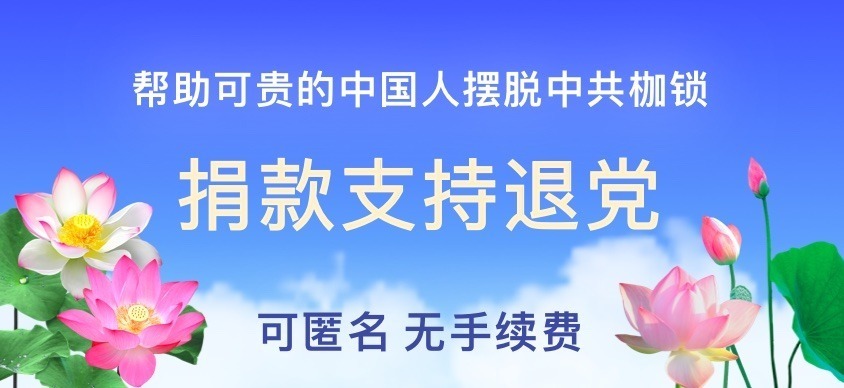我读中学时,受中国教育洗脑,我也曾很爱国。后来去香港读大学,六四时被同学拉去看纪录片,被深深震撼,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政府黑暗的一面。
香港人反送中时,受到中国媒体宣传,我站在了中国一边,参加了和特首的宴会,宴会的邀请函被香港人贴在Telegram群组上,他们威胁要放炸弹。香港警方公开了案情,并说要严惩。我觉得警察是保护我们的。疫情时我还积极响应政府打了科兴疫苗,直到后来才看到香港大学说会导致面瘫。
我毕业后在朱中做老师。在一次和高中同学的约会上发生了矛盾。他对我恶语相向,比不过就想毁掉我,把我挂上网。我向警察报案。中国的警察碍于他家人有权有势,有人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原因,竟草草结案,将案件简单说成是观念不合。他父母还在电话里吼我,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在这绝对权力面前我感到无力。我如此这般爱得深沉,却这么对我。
因为在香港,我没入过党,但我对中国的一切失去信心。我誓言和这连我一名普通人的权益都无法保护的腐朽权力体系彻底断绝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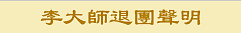
再转轮
当年的单位,必须都是党团员,为此,年青时也被动的被入过团,虽然从来没当回事,也超龄了几十年了,早已不是团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大法:李洪志
·九·评*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
常用工具
退!党!团队服务·通知·倡议
- 1·发表三:退.声明的其他途径:
- (1)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 (2)美国热线电话:
001-702-873-1734
001-866-697-6570
001-888-892-8757
- 加拿大热线电话:
001-416-361-9895
001-514-342-1023
001-604-276-2569
- 台湾热线电话:
00886-906073004
00886-937537422
00886-901012397
00886-901012875
- 香港退!党!热线电话:
+852 65963278
+852 96652626
- 日本退!党!热线电话:
81368067050
- 韩国退!党!热线电话:
82-10-53815957
- (3)各地大.纪.元;报社
- 2·化名退!党!团队同样有效
- 3·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的倡议
此文不计入退!党!总人数
声明人: 钟栩珊
2025-07-29 11:29
广东省东莞市